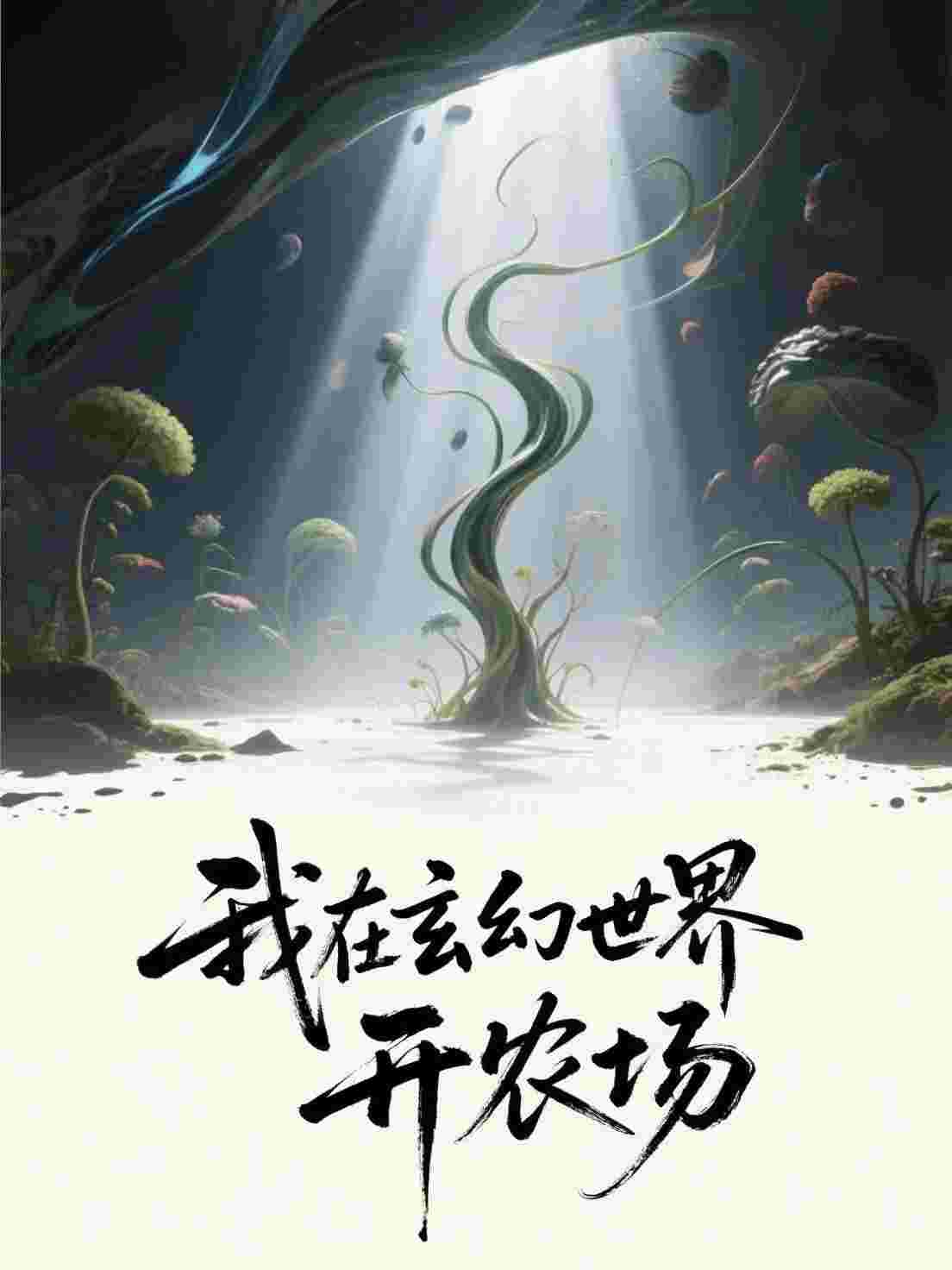首页> > 傻柱重生四合院,开局先杀易中海许大茂秦淮茹免费小说阅读_免费小说大全傻柱重生四合院,开局先杀易中海(许大茂秦淮茹)

小说介绍
《傻柱重生四合院,开局先杀易中海》这部小说的主角是许大茂秦淮茹,《傻柱重生四合院,开局先杀易中海》故事整的经典荡气回肠,属于现代言情下面是章节试读。主要讲的是:在街道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对中年男女走进了院子。男人看起来约莫四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却十分整洁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他的面容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有些憨厚,皮肤是常年奔波在外的风霜色,脸上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平静。然而,若有人仔细看他的眼睛,便会发现那平静之下...
第12章
十天时间,在何雨柱有条不紊的铺垫和李大海(易中海)若有若无的撩拨下,悄然流逝。
这十天里,何雨柱像一头极具耐心的猎豹,每日按部就班地去厂里食堂,颠勺、炒菜,应对着工友们的说笑,一切如常。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步都在为最终的收割做准备。
而李大海,则完美地扮演着阴暗中搅动风雨的角色。
他不再像最初那样急切地鼓动,而是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推心置腹”。
他会趁着给阎埠贵递根烟、帮忙搬个花盆的工夫,压低声音,用那种带着担忧和同病相怜的语气说:“老阎啊,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傻柱那小子,最近看人的眼神不对劲,你说他会不会……”话只说一半,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或者,在阎埠贵因为何雨柱某句意味不明的话而心神不宁时,他会“恰好”出现,拍拍阎埠贵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们现在,可得互相照应着点。”他不断强化着阎埠贵对何雨柱的恐惧,同时又将自己和阎埠贵捆绑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我们是同一战线”的假象。他的每一次“撩拨”,都如同在阎埠贵紧绷的神经上轻轻拨动,让那根弦越来越接近断裂的边缘。
四合院表面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静,洗衣做饭,家长里短,似乎与往日并无不同。
但知情者如阎埠贵,却感觉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尤其是面对何雨柱时,那份强装出来的镇定下,是难以抑制的心悸。
他不敢与何雨柱对视太久,生怕对方从那躲闪的眼神中看穿自己内心的惊惶。
何雨柱每一次从他身边经过,哪怕只是不带任何含义的一瞥,都能让他后背瞬间渗出冷汗,晚上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回放著李大海的警告和何雨柱那看似平常却暗藏机锋的话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恐惧和贪婪在他心里拉锯,让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这天傍晚,夕阳的余晖给四合院染上了一层看似温暖的橘红色。
何雨柱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半旧不新的深蓝色布包,布包看起来沉甸甸的,但又不甚起眼。
他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院内。
前院,阎埠贵正佝偻着腰,小心翼翼地收拾着他的那几个宝贝花盆,用一块旧布擦拭着叶片上的灰尘,但那动作明显有些心不在焉,眼神时不时地瞟向院门方向。
何雨柱嘴角几不可察地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随即隐去。
他停下脚步,支好自行车,拎着布包,像是饭后散步般踱步过去,脚步轻缓,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三大爷,忙着呢?”何雨柱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刻意营造出来的神秘感,打破了前院的寂静。
阎埠贵正神游天外,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他一个激灵,手里那把用了多年的花剪“哐当”一声掉在砖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他慌忙弯腰捡起,心脏怦怦狂跳,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强迫自己转过身,脸上挤出一种极其不自然的、近乎谄媚的笑容,皱纹都堆叠在了一起:“啊,柱子啊,回……回来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何雨柱对他的失态视若无睹,左右看了看,确认院里没有其他人注意这边,这才将手中的布包稍稍向上提起,用一只手拢着,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缝。
那缝隙不大,却刚好让阎埠贵看清里面的东西——三块手表静静地躺在柔软的布衬上,
两块是经典的上海牌,表盘干净,指针清晰,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金属表壳也闪烁着诱人的光泽;
另一块则是略显厚重、风格粗犷的苏联老手表,表盘上的字符带着异域风情,别有一番味道。
“喏,”何雨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是气音,却清晰地钻进阎埠贵的耳朵里,“上次跟您提的那事(傻柱这几天向阎埠贵提过低价出售手表),办成了。大领导家换下来的,看着旧了点,但走时准得很,内部处理,机会难得。”他的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每一个字都重重砸在阎埠贵的心坎上。
阎埠贵的眼睛瞬间直了,瞳孔放大,死死地盯住那条缝隙里的三块手表,呼吸骤然变得粗重起来,胸口剧烈起伏。
他想拒绝,但是……这手表!这成色!这差价!这利润太大了!大到足以让人铤而走险。
黑市上,这种来路正、牌子硬的手表,哪怕是旧的,也是抢手货!
一块就能净赚几十块!三块!
“柱子……这……这怎么好意思……”阎埠贵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喉咙发紧,他感觉自己的手在不听使唤地微微颤抖,却还是不自觉地、缓慢地伸了过去,指尖几乎要触碰到那冰凉的布包。
何雨柱仿佛看穿了他那点心思,在他手指即将碰到的前一瞬,手腕一翻,利落地将布包合拢,那条诱惑的缝隙消失了。
他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三大爷,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东西来路您也知道,我不能留手里,烫手。三块,您给个成本价,一百五十块,您全拿走。至于您怎么处理,我不管,也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他刻意强调了“来路”和“烫手”,既是提醒,也是一种隐晦的威胁,将选择权再次抛回给阎埠贵。
一百五十块!三块手表!阎埠贵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算盘珠子在心里劈啪作响。
哪怕是旧表,拿到黑市,随便一块上海牌都能卖到六七十,那块苏联表说不定更值钱!
这一转手,净赚四十还多!甚至可能更多!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疙瘩!
巨大的利润像一股汹涌的洪流,瞬间冲垮了阎埠贵那本就摇摇欲坠、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心理堤坝。
去他妈的恐惧!有钱不赚是王八蛋!许大茂死了是他命不好!关我什么事!再说了,只要我自己小心点,不去黑市,让解成那小子去,他年轻腿快,能出什么事?
对,让解成去!
这个念头如同救命稻草,让他瞬间找到了规避风险的方法,也让他那被贪婪占据的心灵得到了一丝虚伪的安慰。
“行!柱子,够意思!这情三大爷记下了!”阎埠贵猛地一咬牙,脸上的犹豫和恐惧被一种豁出去的狠劲取代,虽然那狠劲底下还藏着虚弱。
他不再迟疑,匆匆对何雨柱点了点头,几乎是手脚并用地转身冲回屋里,脚步都有些踉跄。
一进屋,他反手就关紧了房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着气,怀里仿佛揣了个兔子。
他哆嗦着走到炕沿边,从最隐秘的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小木匣,打开锁,他手指颤抖着,一遍又一遍地数出一百五十块钱,大多是皱巴巴的零票,毛票,甚至还有几分钱的硬币,厚厚的一沓。
他用旧报纸仔仔细细地包了好几层。
做完这一切,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了一下狂跳的心脏,这才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
何雨柱依旧站在原地,姿态悠闲,仿佛只是欣赏着院里的景色。
阎埠贵走到他跟前,左右张望了一下,迅速将那个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钱卷塞进何雨柱手里,同时几乎是用抢的,一把将那个装着三块手表的布包捞了过来,飞快地揣进自己怀里,紧紧捂住,仿佛怕它长翅膀飞了。
布包隔着薄薄的棉衣,传来冰凉的金属触感,却让他感觉胸口一阵滚烫,心脏砰砰狂跳,既有做成一笔暴利交易的兴奋,更有一种与魔鬼交易后的深深后怕。
交易完成,何雨柱掂量了一下手中钱卷的分量,看也没看就塞进了裤兜。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阎埠贵一眼,那眼神复杂,带着一丝嘲弄,一丝冰冷,还有一丝阎埠贵无法理解的深意。
他没有再多说任何一个字,转身,推起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回了中院。
何雨柱刚走没多久,阎埠贵还沉浸在巨大的情绪波动中,怀里揣着“宝贝”,既想赶紧回屋藏好,又忍不住想再拿出来看看。
就在这时,李大海(易中海)就像一只闻到肉味的猎犬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阎埠贵家门口,脸上带着惯常的、看似温和关切的微笑。
“阎大爷,刚才……我看柱子来找您了?”李大海(易中海)语气自然地问道,目光却如同探照灯般,锐利地扫过阎埠贵那因为揣了东西而略显鼓囊、尚未完全平复下来的胸口,以及他那残留着紧张和兴奋神色的脸。
阎埠贵做贼心虚,被这突然出现的声音和目光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紧紧捂了捂胸口,仿佛那里揣着个炸弹,支支吾吾地掩饰道:“啊……没,没什么,就……就说了两句话,问问我这花长得怎么样。”他的眼神躲闪,不敢与李大海对视。
李大海(易中海)心中冷笑,面上却更加诚恳,甚至带上了一丝担忧:“阎大爷,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有些事,您可千万别瞒我。是不是……柱子给您什么东西了?”他压低了声音,身体微微前倾,营造出密谈的氛围,“我可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点,别让人给‘黑’了!”他刻意加重了“黑”字的读音,暗示意味十足。
阎埠贵被说中心事,脸色瞬间变了几变,青白交错。
他看着李大海那“真诚”而“关切”的眼神,想到对方之前的多次“提醒”,以及现在两人“同仇敌忾”的处境,心理防线松动了一些。
犹豫了一下,他最终还是没敢完全坦白手表的具体数量和交易金额,但也含糊地、带着几分后怕地承认了:“唉,大海兄弟,不瞒你说,是……是有点东西。柱子他……他弄来了点紧俏货,让我帮着……处理一下。”他顿了顿,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的谨慎,又急忙补充道,“不过你放心,我精着呢!我自己不去那地方(黑市),我让我家解成去!年轻人,腿脚快,机灵!准保出不了岔子!”他说这话时,仿佛是在说服李大海,更像是在安慰自己。
李大海心道,让儿子去?这老狐狸,果然狡猾,把自己摘得干净。
不过也好,只要阎家还有人去黑市,就能持续吸引傻柱的注意力,把他拴在这条线上。
他点点头,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用力拍了拍阎埠贵的肩膀,仿佛在鼓励一个勇敢的战友:“这样也好,阎大爷您考虑得周到。让解成去,确实稳妥些。不过还是得千万小心,快去快回,别贪价,安全第一。”他又“好心”地、絮叨地补充了一句,将关心扮演得淋漓尽致。
阎埠贵感受到肩膀上的力度和李大海话语中的“支持”,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连连点头,像是抓住了主心骨:“知道,知道,谢谢大海兄弟提醒!我一定嘱咐好解成!”
李大海(易中海)又宽慰了阎埠贵几句,这才转身离开。
转过身的一刹那,他脸上的“关切”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计谋得逞的阴冷和算计。
他需要阎家继续当这个诱饵,直到彻底把傻柱逼到墙角。
而回到中院的何雨柱,并未立刻进屋。
他站在自家门口,看似在整理自行车,实则集中精神,凭借远超常人的敏锐听觉,隐约捕捉着从前院飘来的、断断续续的对话声。
距离虽远,声音模糊,但阎埠贵那句提高了音调、带着点自得意味的“让我家解成去”,却清晰地钻入了他的耳中。
何雨柱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眼神变得锐利如刀。
阎埠贵这老狗,果然是属狐狸的,奸猾似鬼!
自己不敢冒风险,就让儿子去顶缸?
想得美!真是打得好算盘!
想用儿子的命来填你的贪欲窟窿?
何雨柱眼中寒光闪烁,杀意如同实质般在周身凝聚。
既然你舍不得自己死,让你儿子先替你趟这趟浑水,那就先拿你儿子开刀!
正好,他也想验证一下,阎解成这种在禽兽窝里长大、耳濡目染的“小禽兽”,手上或许还没直接沾太多人命,但骨子里的自私、凉薄和算计已经深入骨髓,不知道系统给不给积分?价值几何?
“既然你让你儿子露头,那便先解决了他!让你这老东西先尝尝丧子之痛,哭上几天!”何雨柱心中杀意已定,冰冷无情,“顺便,看看这些小禽兽,值不值钱!”
计划随之迅速调整。
首要目标从老奸巨猾的阎埠贵,暂时转变为更易下手、且被推出来的阎解成。
方式不变,依旧是利用其前往黑市的习惯,在路上进行埋伏。
接下来的十天,四合院看似恢复了往日的节奏。
阎埠贵在巨大的利润驱动和“让儿子出面”的安全感支撑下,逐渐从最初的恐惧中缓过劲来。
他果然将两块成色较好的手表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大儿子阎解成,自己则偷偷留下了那块看起来最旧、但在他心里或许更值钱的苏联老手表,珍而重之地压了箱底。
阎解成也是个继承了父亲精明算计基因的,突然得到这么“宝贵”的物资,自然是欣喜若狂,绞尽脑汁想卖个最高价。
他开始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出入城南那片鱼龙混杂的黑市,像一只警惕的老鼠,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形形色色的人中间,观察着,试探着,讨价还价。
为了安全起见,他甚至凭借着小聪明,摸索出了一条相对固定、自认为足够隐蔽的往返路线和时间,通常会选择在傍晚天色将暗未暗、人流开始聚集的时候去,待到天黑透、交易最活跃时离开。
这一切,都被暗中密切观察的何雨柱清晰地看在眼里。
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耐心记录着猎物的活动规律、路径选择和行为习惯。
时机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这天,机会终于来了。
厂办通知,傻柱要给杨厂长家做接待宴,也正好是阎解成惯例去黑市的日子。
下午,何雨柱故意在院里,用足以让前院竖着耳朵的阎埠贵听到的音量,对正在洗衣服的娄小娥说:“小娥,晚上我不回来吃了,杨厂长家有重要的接待任务,点名让我去做几个拿手菜,估计得忙活到挺晚。”
下午四点刚过,何雨柱就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装厨具的布包,离开了四合院,径直前往杨厂长家。
他精湛的厨艺再次赢得了满堂彩,煎炒烹炸,香气四溢,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端上桌,宾主尽欢。
杨厂长心情大好,席间还特意把他叫出来,敬了他一杯酒,夸他是厂里的宝贝疙瘩。
何雨柱装作受宠若惊、略带微醺的样子,陪着喝了两杯,脸膛泛红,说话也带着些许“酒意”。
七点多,宴席圆满结束,何雨柱告辞离开。
一出杨厂长家所在那个戒备森严、灯火通明的大院门口,骑上自行车拐过第一个街角,他脸上那层伪装的醉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眼神恢复清明,锐利而冷冽,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烁着寒光。
他骑着车,并未直接返回城南的四合院,而是毫不犹豫地蹬动踏板,绕了一个大圈,穿行在越来越偏僻、灯光愈发昏暗的小巷里,最终来到了通往黑市那条偏僻小路的预定埋伏点——一段不知何年何月废弃的土墙后面。
这里杂草丛生,足有半人高,土墙塌了半截,形成了天然的遮蔽,视野却正好能清晰地观察到小路两头的情况,尤其是从黑市方向返回来的必经之路。
夜色渐深,初冬的寒风呼啸着掠过干枯的草茎,发出呜呜的声响,更添了几分荒凉和肃杀。
何雨柱将自行车收进空间戒指,自己则如同真正融入了阴影的石雕,蜷缩在土墙和杂草的遮蔽之后,呼吸放缓,几乎微不可闻,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辉,死死盯着小路通往黑市的那个方向。
激光手枪那冰凉的触感早已从戒指中传递到他的掌心,被他紧紧握着。
晚上八点半左右,在小路尽头那片更深的黑暗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由远及近,正是阎解成。
他缩着脖子,双手揣在兜里,走路的步伐却带着一种轻快感。
怀里揣着刚刚卖掉一块上海牌手表换来的几十块钱,那厚厚的触感让他心里美滋滋的,不断盘算着剩下那块品相更好的能卖多少钱,是买件新棉袄,还是攒着说个媳妇……各种念头在他脑海里盘旋,让他浑然不觉,前方不远处的黑暗中,死神已然悄然降临,张开了冰冷的怀抱。
就在阎解成低着头,嘴里甚至不自觉地哼起了不成调的小曲,走过那段废弃土墙,将整个后背毫无防备地暴露在何雨柱视线里的那一刻,何雨柱动了!
他如同鬼魅般从杂草和土墙的阴影中无声无息地现身,动作快如闪电,没有带起一丝风声,举起了手中那支来自系统、造型奇特的激光手枪。
没有犹豫,没有怜悯,心中只有一片冰冷的决绝和对系统积分的期待。
瞄准,扣动扳机!
一道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的红色光束,在浓重的夜色中一闪而逝,精准无比地没入阎解成的后心位置。
阎解成向前迈出的脚步猛地一顿,身体剧烈地一僵,脸上那残留的笑容瞬间凝固,变成了一种极致的惊愕和茫然。
他甚至没能感受到太多的痛苦,只觉得胸口像是被烧红的铁钉猛地刺了一下,随即全身的力气如同潮水般退去。
他想呼喊,喉咙里却只发出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鸡一样的“咯咯”声,连一声像样的闷哼都没能发出,便向前重重地扑倒在地,脸部撞击在冰冷坚硬的土地上。
他的四肢无意识地抽搐了两下,便彻底瘫软,再无声息,圆睁的双眼里还残留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突如其来的困惑。
他怀里那还没捂热乎的、用卖表钱换来的一小卷钞票,也散落了出来,沾上了泥土。
何雨柱迅速上前,蹲下身,伸出手指在阎解成的颈动脉上停留了片刻,确认死亡。
然后,他毫不拖泥带水地将阎解成尚带余温的尸体,以及散落在地的那卷钞票,一并收进了空间戒指。
激光手枪发射时产生的高温再次起到了作用,瞬间碳化了伤口,确保了没有一滴血液喷溅出来,现场干净得令人发指。
他站起身,借着微弱的天光,仔细地清理了一下现场,将自己可能留下的脚印用脚抹平,又将旁边几丛被自己压弯的杂草小心扶正。
做完这一切,他如同来时一样,沿着另一条更加偏僻、绕远但绝对安全的路线,迅速撤离了现场,身形很快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
在他离开后不久,正快步走在返回四合院的路上,脑海中如期响起了那冰冷的、毫无感情的提示音:
消灭禽兽阎解成,奖励一亿积分
何雨柱疾走的脚步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真正的惊讶,但随即这惊讶便化为了更深的冰冷和了然。
果然如此!这些从小在禽兽窝里长大、被言传身教的小崽子,哪怕手上还没直接沾染人命鲜血,但其骨子里继承的自私、凉薄、算计和那种损人利己的根性,已然让他们成为了合格的、纯粹的“禽兽”,同样被系统认可,价值一亿积分!
这个结果,让他内心深处对清理整个四合院,包括那些尚未完全长成但已显露出禽兽本质的小辈,再无任何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
这不再是复仇,更像是一场彻底的、正义的净化。
第二天,阎解成彻夜未归。
起初,阎埠贵还以为是儿子在朋友家借宿了,或者卖表顺利,在外面吃了点好的,甚至可能去看场电影犒劳自己(虽然以阎解成的抠门性子可能性不大)。
但直到日上三竿,中午饭点都过了,还没见阎解成的人影,他心里的不安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
手表才卖出去一块,自己手里留了一块压箱底,解成身上可还有一块品相最好的上海牌啊!
那可是一大笔钱!
他再也坐不住了,强作镇定地出门,沿着儿子可能去的地方找了一圈,问了几家相熟的和阎解成可能去的朋友家,得到的都是摇头和否定的答案。
一种熟悉的、冰冷的恐惧感如同毒蛇般再次从脚底窜起,死死地攫住了他的心脏!手脚瞬间一片冰凉。
解成……难道也……步了许大茂的后尘?
这个念头如同惊雷般在他脑海里炸开!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何雨柱!是傻柱!一定是他!他杀了我的解成!
阎埠贵几乎要疯狂了,恐惧和丧子之痛(他几乎已经认定)交织在一起,让他浑身发抖。
他像疯了一样冲到了派出所报警,语无伦次地说儿子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家,最后可能是……可能是去了黑市,身上带着值钱的东西。
接待他的警察一听“黑市”,又听说可能是去倒卖手表,脸上顿时露出了“了然”和“不耐”的神情,这种在黑市交易中被黑吃黑、卷货跑路、甚至人间蒸发的案子,他们见得太多了,根本无从查起,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管这些“自找”的麻烦。
警察草草地做了记录,例行公事地询问了阎解成的体貌特征、最后出现的大概时间和地点,便打发阎埠贵回去等消息,那态度几乎是明摆着的不了了之。
阎埠贵失魂落魄、步履蹒跚地回到四合院,看着空荡荡的、少了儿子的屋子,想着生死不明(他内心已经认定死了)的阎解成,想着那损失的两块手表和已经到手的钱财(他以为一起没了),顿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捶打着胸口和炕沿,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嘶哑:“我的儿啊!你怎么就……就这么没了啊!我的表!我的钱啊!人财两空!人财两空啊!这可叫我怎么活啊!”哭声凄厉,在四合院里回荡,引来了不少邻居的侧目和议论,但真正同情的有几个,就未可知了。
就在这时,李大海(易中海)再次“适时”地出现,仿佛一直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他走进阎家屋子,看着阎埠贵这副涕泪横流、捶胸顿足的凄惨模样,心中冷笑不止,脸上却堆满了深切的同情和共情般的愤慨,他上前一步,扶住阎埠贵的肩膀,痛心疾首地说:“阎大爷!节哀啊!节哀!千万保重身体!我就说嘛!傻柱他肯定有问题!现在解成兄弟也……唉!这杀千刀的傻柱,这是要赶尽杀绝啊!”他的话语充满了煽动性,将阎埠贵的悲痛直接引向了何雨柱。
阎埠贵猛地抬起头,一把抓住李大海的胳膊,如同一个即将溺毙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眼睛布满了血丝,通红一片,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大海兄弟!是他!一定是傻柱!他杀了我的解成!他这是报复我!可……可我没证据啊!警察也不管!他们根本不管黑市那些破事!我该怎么办啊?我的解成死得冤啊!”他摇晃着李大海的胳膊,绝望地嘶吼。
李大海(易中海)反手用力握住阎埠贵冰冷颤抖的手,眼神闪烁着阴狠毒辣的光芒,压低声音,如同从地狱传来的魔鬼低语,充满了诱惑和鼓动:“阎大爷!光哭没用!哭能把解成兄弟哭回来吗?报警没用,指望不上他们!咱们就自己来!自己给解成报仇!”
“自己来?”阎埠贵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泪眼模糊地看着李大海那骤然变得凶狠狰狞的脸。
“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李大海(易中海)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一种豁出去的疯狂,“他傻柱不是喜欢在黑市路上动手吗?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请他入瓮!”
他凑到阎埠贵耳边,几乎是贴着耳朵,用极低的声音,详细而清晰地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恶毒计划:“你,听着,阎大爷!你继续去卖剩下那块手表!就你自己去!不能再让家里人冒险了!我会悄悄跟在你后面保护你!我手里有这个——”他说着,悄悄掀开棉衣的一角,露出了别在腰间那支老旧手枪,“到时候,你只管往前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跟平常去黑市一样。如果傻柱真的出现,要对你下手,你看见他,别犹豫,转身就拼命往回跑!大声喊也行,总之吸引他注意力,让他来追你!剩下的,交给我!”他拍了拍腰间的枪柄,眼中凶光毕露,“我在后面,找好位置,用手枪解决他!就在黑市路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为你家解成报仇!到时候就往黑吃黑上一推,谁查得出来?”
阎埠贵听着这个详细而大胆的计划,心脏狂跳,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脸色煞白如纸。让自己去当诱饵?
亲自面对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傻柱?
这太危险了!
简直就是送死!
但看着李大海那“坚定”、“可靠”甚至带着几分“同归于尽”决绝的眼神,感受到他话语中那股强大的煽动力,再想到儿子惨死(他认定)的悲愤,想到傻柱如此嚣张、接连害人(在他看来)的滔天怒火,一股巨大的、近乎疯狂的仇恨和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勇气(或者说被逼到绝境的绝望)猛地涌了上来,瞬间淹没了恐惧。
傻柱必须死!他不死,下一个死的肯定就是我!他不会放过我的!
与其整天提心吊胆,不如拼了!
有大海兄弟在后面拿着枪保护,应该……应该没问题吧?他枪法怎么样?……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猛地一咬牙,脸上肌肉扭曲,露出了狰狞而决绝的神色,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但又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狠厉:“好!大海兄弟!我听你的!就这么办!跟他拼了!为解成报仇!咱们……咱们什么时候动手?”他的声音因为激动和恐惧而微微颤抖,但意思却无比明确。
李大海(易中海)眼中闪过计谋得逞的冰冷光芒,但他控制得很好,脸上依旧是同仇敌忾的表情:“不急,阎大爷,不能太明显。傻柱刚动了手,现在肯定警惕。等过上三五天,风声稍微过去一点,他也放松警惕了,咱们就行动!这几天,你正常上下班,该干嘛干嘛,别在傻柱面前露破绽,别让他起疑心。”
“好!我都听你的!大海兄弟,全靠你了!”阎埠贵重重地点了点头,浑浊的眼里闪烁着泪光、仇恨和一丝虚幻的希望,仿佛已经看到了傻柱在李大海的枪口下血溅当场、为他儿子偿命的情景。
两个各怀鬼胎的人,一个被丧子之痛和贪婪反噬逼入绝境,一个复仇之心、极力煽动,在这间被悲伤与仇恨笼罩的房间里,定下了一个针对何雨柱的死亡陷阱。
为您推荐
小说标签